|
|
2024年于北京時間27日淩晨1:30正式開幕。有别于過往在體育館舉辦的傳統,這屆開幕式沿塞納河兩岸舉行,超過30萬名觀衆在塞納河畔觀看儀式。
在開幕式中,十座鍍金雕像從塞納河畔緩緩升起,該章節旨在頌揚法國曆史上的傑出女性代表,被命名爲“Sororité”(女性友誼)。十位女性的職業各異,有起草女性宣言的政治家,有創辦女子運動會的優秀運動員,有維護女性合法權益的律師,有爲女性權益而奮鬥的作家,有倡導不同種族女性平權的記者,有首位實現環球航行的女探險家,等等。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其中一位傑出女性——納粹大屠殺幸存者、女性政治家西蒙娜·韋伊的人生。西蒙娜·韋伊是納粹大屠殺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是賦予法國女性堕胎權的立法者,也是緻力于實現歐洲和解與團結的政治家。在韋伊的自述《比克瑙集中營的黎明》中,我們看到了一位傑出女性堅韌不拔的靈魂。而在這強有力的性格背後,是慘痛的集中營遭遇。雖然我們無法真正感同身受,但是韋伊爲我們提供了一套帶着傷痛前進的方法:不要停下做事情的腳步,并且相信自己可以擁有正常的生活。
西蒙娜·韋伊(Simone Veil,1927.7.13-2017.6.30)生于法國尼斯,奧斯維辛集中營幸存者。法國衛生部前部長;歐洲議會前議長,也是第一位女性議長;法國憲法委員會前成員。1998年獲得英國ZF的榮譽勳章(DBE)。2008年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死後葬入法國先賢祠,她是曆史上第五位被安葬在先賢祠的女性。
1944年4月,西蒙娜·韋伊和家人被押往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
在集中營裏,黨衛軍在新來的囚徒的手臂上文上編号,并将處于驚懼之中的人們送往一間間磚砌的長條棚屋。
勞役期間,面對那些擔心親屬命運犯人的問詢,卡波們(Kapo,與納粹合作的囚犯,他們在納粹集中營中擔任領導或行政職務)會直截了當地回答:“之前和你們在一起的那些人......看看那些煙囪吧,他們都進了毒氣室,屍體已被焚化。剩下的就是這些灰了。”西蒙娜在自述《比克瑙集中營的黎明》中講道“那股持續不散的味道。近在咫尺,揮之不去......”
在奧斯維辛,時年17歲的韋伊,看到了人可以非人到何種程度。直至西蒙娜·韋伊步入老年,某種特殊的味道,一絲寒冷,哪怕一個幻象都能讓她産生一種被她稱爲閃回的東西,勾起模糊而殘酷的記憶。這種情況總是來得猝不及防。“有時,一個起初看起來非常正面,甚至是幸福的畫面都可能會引發焦慮。哪怕看着一群孩子都能把我帶回大屠殺的年代”。
西蒙娜·韋伊在集中營總共待了十三個月,而多的是比她待得更久的人。韋伊的母親在1945年解放前夕死于傷寒,父親和哥哥被送往立陶宛後再也沒能回來。韋伊和妹妹活了下來,但妹妹在戰後不久就死于車禍。在西蒙娜·韋伊看來,沒有什麽能和這段經曆相提并論。“在我們能讀到的和人們能寫出來的東西與那種絕對的恐怖相比,根本就是小巫見大巫。”在自述《比克瑙集中營的黎明》裏,韋伊說。
戰後,韋伊帶着無法抹去的記憶創傷前進,她在巴黎政治學院學習法律和政治學,之後進入政界。1954年,她通過司法考試,成爲了一名法官,并處理了阿爾及利亞的監獄問題。
1974年11月26日,法國國民議會開啓了讨論關于流産的計劃法案,時任衛生部部長的西蒙娜·韋伊在國民議會發表45分鍾強有力的講話,随後在講台上連續3天,力辯以男人爲主、敵視堕胎的數百位議員,連同**在議會外抗議殺生的神甫和不明真相的婦女,要他們正視每年三十萬例非法堕胎的現實,以及由此而生的無盡的羞辱和創傷,最終推動議會在29日通過了“韋伊法”——《自願終止妊娠法》,使法國成爲第一個堕胎合法化的主要的天主教國家,對現代法國的婦女解放和世俗主義意義重大。
以下爲西蒙娜·韋伊的自述,節選自《比克瑙集中營的黎明》
“男人恐怕很難讓這部法案得以順利通過”
1974年,德斯坦在總統競選時提出要讓自願終止妊娠合法化。當選之後,他便着手促進這個計劃的實現。在以希拉克爲首的内閣中,讓·勒卡尼埃(Jean Lecanuet)任司法部部長,我是衛生部部長。在促進自願終止妊娠合法化這件事上,德斯坦更傾向從公共衛生而非司法的角度切入。指針已向我傾斜。不僅如此,總統還認爲這樣一個計劃由一個女性來辯護更容易。而且,他在這件事上非常堅定,毫不猶豫地推行這一計劃。他的内政部長,米歇爾·波尼亞托夫斯基(Michel Poniatowski)之前一直在提醒他:非法人流已呈泛濫之勢并對日常社會秩序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西蒙娜·韋伊與希拉克在奧斯維辛集中營
當時的總統多數派裏包含有中間派、戴高樂主義者和基督教民主黨,這些人中反對這一計劃的不在少數。就連總理雅克·希拉克一開始也并不看好這一議案。他覺得這不過是總統的突發奇想。由于充分了解該議案在其陣營中是多麽的不受歡迎,他不是很明白我爲什麽要如此堅持。可當ZF做出決定後,該議案就變得勢在必行了,必須要通過立法投票。
之後,希拉克開始給予了我全方位的支持。首先,是精神支持。他經常給我打電話。其次,是政治支持。當需要對法案進行一些修正,尤其是那些與自願終止妊娠相關的修正時——這非常重要——他總會站在我這邊。
在議案投票結束後,我覺得周邊,無論是我身邊還是更爲上層的政治圈,尤其是總統多數派的一些成員,對我的态度開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并非立刻出現,因爲大部分人認爲我的聲望肯定是昙花一現。很多人說:“人們是注意到她了,可她始終是個新人,這種聲望維持不了幾個月。她有那麽重的文書工作要做,最終一定會以失敗告終。”那時,很少有女性會在政治上冒險。
可出人意料的是,我的聲望不但沒有減弱,還得到了民調的證實,并且随着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強。專家們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高的聲望可以延續這麽久。哪怕之後我不再涉足法國政壇,我的民望依舊。這無疑讓我所屬的政治陣營産生了某種不快。一些人私下會說:“無論如何,西蒙娜·韋伊是個連話都說不清楚的笨嘴葫蘆,無知透頂。她就是傻人有傻福。她就會煽情,知道怎麽在民衆面前哭,這是她唯一會做的事......”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我已經對一些事情習以爲常了:我在左派中的形象遠比在一些保守的右派中要好得多。在後者這個圈子裏,經常有男性對我說:“我的夫人非常崇拜你!”原話就是如此。好像隻有女人可以欣賞其他女人一樣......
1977—1978年間,很多人擔心自願終止妊娠法案的成功會讓我一舉登頂。人們擔心我會因此生出不該有的野心,危及我們這一陣營中的其他候選人。1979年,當歐洲議會首次舉行普選時,德斯坦讓我代表“法國民主聯盟”政黨(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簡稱UDF) 參選。當我成爲歐洲議會主席,離開法國政壇後,有些人如釋重負。
後來,一些人,或者說一些女性,總試圖讓我回歸法國政壇,甚至提出讓我參選法國總統。這種提議通常都來自女性,她們總說不能讓事情再這樣下去了,必須要繼續爲女性主義抗争。直至今日,每當有選舉,總有人給我寫信:“法國需要您。”确實,在198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我領導的右翼聯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我們取得了43%的選票,并成功成爲歐洲議會中的絕對多數。這無疑是一次完勝。不過,法國右派卻極力降低這次勝利的影響。我又一次意識到自己踩到了一些天然盟友的痛點。他們生怕我會以總統寶座爲目标,強勢回歸法國政壇。确實,在法國機構裏,一切都圍着總統的位置轉,好像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的政治目标了。
當時,若是我參加了某個政黨,或是積極參與某些活動,抑或有什麽很重要的責任需要承擔,我或許會投身這場戰鬥,哪怕就是爲了讓一個女人成爲總統候選人似乎也是個不錯的理由。可我完全不想加入任何一個政黨。這與我本性不符。要做出太大的犧牲。
我承認,我的政治生涯确實是一帆風順,甚至可以說如有神助。我選擇了獨立。因爲我從不覺得自己能夠服從某個政黨的紀律,或是成爲一個好的鬥士。我太愛提意見了。當我進入一個組織,我必然會提一些意見......哪怕會讓人震驚,甚至引起誤解。我曾經屬于右翼聯盟,可很多左派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可若我屬于左派聯盟,右派人士大約也會說:“爲什麽她不加入我們?”我學會了如何在邊緣生存,然後就一直處于這種狀态。這很符合我的本性。
在我提出某個議案時,我總會設想自己是反對派的一員,然後将自己的議案批得體無完膚。很多時候,我覺得那些攻擊我的言論實在是太沒有水平了。我自己的批評比他們的要好得多。哪怕是我自己提出的議案,我也很快就會提出抗議。反正,這些議案最後也從來不曾像我設想的那樣。不過,我也承認,當有人批評我時,哪怕是一些具有建設性的意見或僅僅就是一些建議,我的第一個反應也大多會是“不”。更準确一點,我會說:“不,不過我會看看。”這個“不”其實是一種不信任的否定。我害怕被人左右,失去控制權。我的心态很難解釋:懷疑是我的天性,但是在一些問題上,我又極爲堅持。我經常聽人說:“簡直沒法和你商量!”
一些時刻被我挂在心上的事情,這五十多年來已經被我反複思量多次。懷疑它們會讓我極爲痛苦。
我也經曆過一些激烈的沖突,包括和我同陣營的一些人。在自願終止妊娠議案的辯論中,我看到不少自己非常喜歡和尊敬的人突然變得聲色俱厲。他們對我口誅筆伐,說出來的話遠超我的想象。要是這些批評來自一個與我而言毫不重要,毫不相幹的人,我完全不會有什麽感覺。可若是那些我十分尊敬的人這麽說我,我就會被傷得很深。
米歇爾·德勃雷就是個例子。出于人口學的考量,他非常反對自願終止妊娠的議案。他認爲這将對法國的生育率造成極大的影響。他是一個堅定的反對者,但他對我本人和觀點始終保持尊敬。他的語氣和用詞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一些與我相識或不相識的公衆人物則對我進行了非常猛烈的攻擊。這些人中不僅有我的政治同盟,也有一些我十分尊敬的人,我們也曾一度交好。他們用極其粗暴的語言攻擊我。讓我覺得哪怕議案的發起者是個男人,辯論都不會這麽艱難。話說回來,男人恐怕很難讓這部法案得以順利通過。
西蒙娜·韋伊(Simone Veil)和丈夫安東尼(Antoine)的棺木進入先賢祠,2018年7月1日,巴黎 ®REUTERS/Philippe Wojazer
除此之外,還有排猶主義。無論是在堕胎法案的辯論階段,還是投票階段,甚至是法案通過後的那幾年,我都曾收到侮辱性的信件。打開信件碰到一些侮辱性的語言或惡劣的圖畫可不是什麽讓人愉快的事......這些信件我保存了大部分。可惜,沒能全部留存下來。我的秘書們最後向我坦誠,一些信件的内容實在過于可怕,她們看完就馬上撕掉了。還有很多信件是在我離開ZF部門之後才送達。我本應更爲警惕,讓部裏幫我保管這些信件并對其進行分類。大量此類信件都被銷毀了。
我保留了很多包含排猶主義内容的信件。這些信上都标有反萬字符和辱罵之語。自從提出自願終止妊娠法案之後,這種信件就未曾斷絕。不過,我要強調的是,不是所有反對這一法案的人都是排猶主義者,這兩者并不能混爲一談。不過,确實有很多排猶主義者借着反對法案的名義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詞。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提出自願終止妊娠法案之後,我就遭到了“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的猛烈抨擊。當時他們還處于政壇的邊緣,宣揚起排猶主義來也比現在更加露骨大膽地多。我對這些攻擊毫不在意。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當對手已經無可救藥且令人反胃時,他也就無法觸及你本人。讓人擔憂的是,有那麽多的人被這個政黨牽着鼻子走,爲他們投票,甚至搞不清楚他們代表的到底是什麽。
後來,排猶主義言論也會出現在和我相關的其他争論之中。1993年,歐洲議會對是否允許在動物身上試驗化妝品展開了激烈的争論。作爲歐洲議會的前議長和現任議員,我收到了成千上萬封要求禁止一切動物實驗的請願書。那時最重要的動物保護協會都使用動物大屠殺,後來甚至用上了動物滅絕這種詞彙。他們開始與一些曾受過納粹迫害的歐洲議員接觸,并直接聯系上了我。他們是特意找的我,因爲在這種背景下,我似乎自帶環保的色彩,擁有一種不會因紛雜政見而卻步的同情心。
至于帶有排猶主義色彩的人身攻擊,這些年來已經少了很多。也許是因爲排猶主義已轉向他途,以其他的形式呈現;也或許是因爲我的敵人們不敢繼續從這種角度來攻擊我。
好在,任何事物都有兩面。今天,關于自願終止妊娠法的讨論已被收入學校的教材。對于很多人來說,這件事情已經成爲曆史。有時,當有人找我簽名時,我會和一些家庭面對面。年輕人看着我尚在人世甚爲驚訝。對于他們來說,我已經是個曆史人物,一個過去的人物......另外,發表人物傳記,做人物訪談,這不一般都是等人物蓋棺定論之後才會做的事嗎?
相關推薦
[法] 西蒙娜·韋伊 口述
[法] 大衛·泰布爾 整理
張潔 譯
活字文化 策劃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2年6月
本書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由西蒙娜•韋伊紀錄片的導演叙述,第二部分爲西蒙娜·韋伊自述,第三部分爲西蒙娜·韋伊與朋友們的談話。其間配有紀錄片劇照與西蒙娜•韋伊兒時的照片,共計60幅。
西蒙娜·韋伊曾經擁有一個快樂的童年,進入集中營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經曆了摧毀人性的暴力和骨肉分離的悲痛,看過了人可以非人到什麽程度,韋伊的心靈被蒙上永久的陰影,一如手臂上的文身。
在本書中,韋伊全面講述了集中營前後的經曆,慘痛的遭遇我們無法真正感同身受,但是韋伊爲我們提供了一套帶着傷痛前進的方法:不要停下做事情的腳步,并且相信自己可以擁有正常的生活。除此以外,奧斯維辛幸存者的視角也是饋贈給讀者珍貴的禮物,當她談起自己的遭遇、掙紮和努力時,是在用個人的經曆書寫一段曆史,雲淡風輕之下有一股深邃而超拔的力量,正是這股力量助她走上政壇,也是這股力量打開了女性被壓抑的種種可能性。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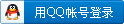
×
|